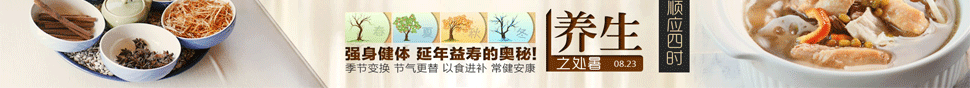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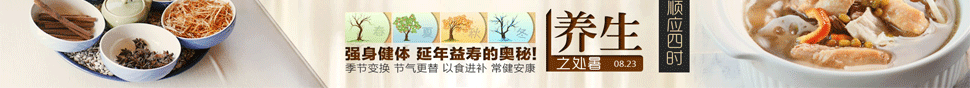
“千年人参,百年陈皮”。陈皮的药食利用非常普遍,历史极为悠久,其中尤以广东新会出产的广陈皮最为有名,“新会陈皮”作为新会的一张名片,享誉海内外。
传统中药陈皮因道地广东得名广陈皮,亦称为“广皮”、“广橘皮”,是陈皮中的上品,而新会陈皮又是广陈皮中的臻品,主要是用地道正宗的新会大红柑、大蒂油身柑、油身仔(关于为何本文不称“茶枝柑”(年王浩真)以及新会柑的品种、名称、渊源另文介绍)的果皮晒制、陈放而成,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
一、陈皮名称考证
经查阅历史文献可知,我国利用柑橘的外皮食用和作中药,约有年的悠久历史,只不过在旧文献资料中,往往不是以“陈皮”的字眼出现,“陈皮”的名称在元代以后才变得常见。陈皮名称的具体演进过程及相关文献记载如下:
“橘”,历史上的“橘”,囊括了现代的柑、桔、橙、柚、柠檬等品种类群,但先秦、两汉的记载中只称橘柚,例如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小曰橘,大曰柚”;《周礼·考工记序》有“橘逾淮而北为枳”的著名典故;著名诗人屈原的楚辞诗歌《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传兮”传诵千古;《史记》中有“橘柚芬芳”、“橘柚之园”的记载;《全唐诗》中出现“橘柚”的诗有40首,例如柳宗元《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中的“橘柚玲珑透夕阳”等。
“柑”,是由于“橘”所包含的种类较多,后来其中的“柑”因其经霜成熟后,果味甘而被称为“甘”,因属木本植物而加木字偏旁为“柑”,从而在“橘”中独立分离出来。两晋时嵇含著《南方草木状》中已见“柑”的出现,并将“柑”与“橘”分别记述:“柑,乃橘之属,滋味甘美特异者也”。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宋书》、《南史》写作“甘橘”;《旧唐书》、《新唐书》中已称“柑橘”,从中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柑”的演进过程。而《全唐诗》中亦有十几首出现“柑”的诗句,其中有“柑树”、“柑橙”、“柑园”、“柑子”、“黄柑”等词汇,如杜甫诗《树间》“岑寂双柑树、婆娑一院香”、杜牧《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越浦黄柑嫩、吴溪紫蟹肥”、韩翃《家兄自山南罢归献诗叙事》“黄苞柑正熟,红楼鲙仍鲜”。《全宋词》中“柑”字出现得更多,约有40首,例如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辨,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和张孝祥《水调歌头》“家种黄柑丹荔,户拾明珠翠羽,箫鼓夜沈沈”、苏轼奇文《记峻灵王庙碑》“山有石池,产紫鳞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多荔枝、黄柑,得就食,持去,则有风雹之变”等。
二、陈皮功效考证
2.1现存陈皮用药考证
古人在种植、食用柑橘过程中,经过实践逐渐发现其外皮具有药用价值,可用于治疗疾病。从传世的本草、医书和药典中,我们不难发现历代对陈皮的认识、功效和应用是一个不断扩大和完善的过程:
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医药学经典顾观光所著《神农本草经》卷一记载:“橘柚一名橘皮,味辛、苦、性温,归脾、胃、肺经。生川谷。治胃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东汉未年医学家张仲景总结汉以前的医学经验,写下了传世的《伤寒杂病论》,其中的《金匮要略》中就有不少应用橘皮的药方。(注:这一时期橘皮主要用于治胃热,功效为理气、健脾、消食)。
魏晋南北朝时期,陈皮的功效除了理气以外,还有止泻和利尿等功效。据魏晋时期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记载:“无毒,主下气,止呕咳,治气冲胸中,吐逆霍乱,疗脾不能消谷,止泻,除膀胱留热,下停水,五淋,利小便,去寸白。久服轻身长年。生南山,生江南,十月采”(本经原文:“橘柚,味辛,温,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一名橘”)。此外,人们开始发现“橘皮”作为中药,干燥陈放日久的“陈皮”药效更好。例如,陶弘景云“橘皮疗气大胜,以陈久者良”,并在《本草经集注》中记载六味中药须陈用,“凡狼毒、枳实、橘皮、半夏、麻黄、吴茱萸皆须陈久者良,其余须精新也”。刘宋、雷学所著的《雷公炮炙论》橘皮篇记载“雷公云:凡使,勿用柚皮、皱子皮,其二件用不得。凡修事,须去白膜一重,细锉,用鲤鱼皮裹一宿,至明,出,用。其橘皮,年深者最妙”。晋葛洪撰《肘后备急方》的多个方子中亦有“橘皮”、“陈橘皮”的药名。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医学家已精通和广泛使用陈化的橘皮入药,并认为药效更佳。(这一时期增加了止咳、利尿的功效,开始注重陈用和区分去留白功效)。
隋唐时期,橘皮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是化痰止咳,如《本草拾遗》:“能去气调中”;《药性论》“橘皮,清痰涎,开胃。治上气咳嗽,主气痢,破癥瘕痃癖,治胸膈间气”,以及《日华子本草》记载“橘皮,暖,消痰止咳,破癥瘕痃癖”。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很多采用橘皮的方剂,且其在《千金食治》中重点提到橘皮“入药以陈久桔皮辛辣气稍和为佳”。但真正首次明确提出“陈皮”这一称谓的,是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孟诜在开元年间撰写我国第一本食疗专著《食疗本草》(具体成书年间不详),其中不但对“柑子”的药性、功效进行了论述,还对橘、橘皮、陈皮的药性、功效、使用方法展开了论述,例如卷上·柑子(乳柑子)〈寒〉中记述“(一)堪食之,其皮不任药用。初未霜时,亦酸。及得霜后,方得甜美。故名之曰甘〔心·证〕。(二)利肠胃热毒,下丹石,(止暴)渴。食多令人肺燥,冷中,发流癖病也。〔心·证〕”;卷上·橘〈温〉中记述“(一)(穰):止泄痢。食之,下食,开胸膈痰实结气。下气不如皮也。穰不可多食,止气。性虽温,甚能止渴。〔心·嘉〕。(二)皮:主胸中癖热逆气。〔心〕(三)又,干皮一斤,捣为末,蜜为丸。每食前酒下三十丸,治下焦冷气。〔嘉〕(四)又,取陈皮一斤,和杏仁五两,去皮尖熬,加少蜜为丸。每日食前饮下三十丸,下腹脏间虚冷气。脚气冲心,心下结硬,悉主之。〔嘉〕”。而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记载的饮茶方式“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则是陈皮用于饮食的首次文字记载。(这一时期明确提出止咳、化痰的功效,首次提出陈皮的概念)。
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本草的研究和发展,宋代史料笔记《泊宅编》云“橘皮宽膈降气,消痰逐冷,有特殊功效”,提到陈皮利肺气、祛痰驱寒的功效;陈言撰《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四库全书本),卷十四中有一个方剂三白散:“白牵牛二两,白术、桑白皮、广皮、木通各五钱右为末,每服二钱姜汤调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卷十一中记载:“实脾丸:干山药一斤,炒黄色为末,炒粳米二升一半,为煳丸米汤送下,白淋广皮一斤,枳壳五两,麸皮炒黄木香不见火,三两黄连,三两姜……”、“嘈杂吐清水,上好广皮去白为末,五更起坐床上,安末五分于手心,男左女右干舐下,而卧服三朝必効。”。此时,关于陈皮陈用的论述出现频率亦逐渐趋多,例如苏颂著的《本草图经》云“收之并去肉,暴干,黄橘以陈久者入药良”;王继先著《绍兴本草》亦云“唯橘皮以陈久者佳”;王袞撰《博济方》,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撰于年)、王璆的《是斋百一选方》(撰于年)、李迅《集验背疽方》(撰于年)中亦曾采用“陈橘皮”、“青橘皮”“真橘皮”、“真陈皮”等。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宋代不同医家的不同验方中多次出现了“真橘皮”、“真陈皮”的提法和用法,虽然“真橘皮”、“真陈皮”具体是什么样的陈皮在宋代医学典籍和历史文献都未直接明言,也未能找到相关资料。但可以推断“真橘皮”、“真陈皮”肯定是一味道地药材。根据宋代吴彦夔《传信适用方》·卷上(年):“法制槟榔治酒食过度,胃膈膨满,口吐清水,一切积滞,洪子和传鸡心槟榔一两切作细块,白豆蔲取仁一两,缩砂取仁一两,拣丁香一两切作细条,粉草一两切作细块,生姜半斤切作细条,盐二两,真陈橘皮半斤(去白),切作细条右件,同河水两碗浸一宿。次日用慢火砂锅内煮干,焙干,入新瓶收,每服一撮细嚼酒下。”;李迅《集验背疽方》不分卷(撰于公元年)·论服嘉禾散中记载:“陈橘皮:买真橘皮,以水浸三时久,洗去黑尘,掠去肉白筋与瓤,剉焙取三两净。”;杨士瀛《仁斋直指》(公元年)·卷七·呕吐·呕吐证治:“翻胃方:橘皮汤治翻胃呕吐,真橘皮用日照西方壁土炒香,取橘皮为末右,每二钱姜枣略煎服”;“南木香、甘草(炙)、青木香、吴茱茰荡洗七次炒乾各半两,宣木、真橘皮、紫苏茎叶、鸡心槟榔各一两右,剉散。每服三钱,姜五片。”。在此,笔者大胆设想,如果“真橘皮”不是道地药材的话,没必要特意注明为真,也没必要特意去买,更无必要把“真橘皮”放在“陈橘皮”的条目下面加以解释说明,直接说“陈橘皮”就可以了。这里关键在于一个“真”字,“真”的才是道地的。(这一时期陈皮陈用的观点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宋元丰5年(公元年)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有“今医方乃用黄橘、青橘两物……,然黄橘味辛,青橘味苦……,而今之青橘似黄橘而小,与旧说大小、苦辛不类,则别是一种耳。……而青橘主气滞,下食,破积结及膈气方用之,与黄橘全别”的记载,但青皮首次出现在医籍中,并载明功效是始载于宋淳熙13年(公元年)张元素所著的《珍珠囊》(张元素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创立中医易水学派,最早创立药物归经说),云“青皮主气滞,破积结,少阳经下药也。陈皮治高,青皮治低”。在其所著另一部医学教科书《医学启源》中其详述了陈皮和青皮的性味功用:“橘皮气温味苦,能益气。加青皮减半,去滞气,推陈致新。若补脾胃,不去白;若理胸中滞气,去白。《主治备要》云:性寒味辛,气薄味厚,浮而升,阳也。其用有三:去胸中寒邪一也。破滞气二也。益脾胃三也。少用白术则益脾胃;其多及独用则损人。又云:苦辛,益气利肺,有甘草则补肺,无则泻肺。”、“青皮气温味辛,主气滞,消食破积。《主治秘要》云:性寒味苦,气味俱厚,沈而降,阴也。其用有五:足厥阴、少阳之分,有病则用之一也。破坚癖二也。散滞气三也。去下焦诸湿四也。治左胁的积气五也。”、“主治备要云: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经曰:虚则补其母。水能生〔木〕,水乃肝之母也。”。张元素的医药学理论和对陈皮、青皮药效的认识影响至深,其弟子李东垣、徒孙王好古等人均在其基础上加以传承和发展,并成为一代名医大家。(这一时期青皮在本草首次出现,开始区分陈皮、青皮以及去白、留白的不同功效)。
2.2新会陈皮用药考证
除了在医典药书中频繁出现,宋代佛教巨著《五元灯会》、李昉等人所著文言纪实小说《太平广记》等著作中也曾提到“橘皮汤”,由此可见,当时陈皮已在民间广泛用于入药和食用。此外,相传新会专门种柑取皮在宋代已有,但一直规模不大。据《广州府志》·卷七·沿革表二·新会县沿革考“广南东路广州南海郡新会〔宋史地理志〕。”的记载,新会在宋元时期属广南所辖。而根据宋代庄绰著《鸡肋编》·卷下:“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竢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以及元成宗大德八年(年)的《南海志》卷七《物产》“柑子,有源柑、银柑。有馒头柑,以小尖如馒头,香味不减温柑”的记载,虽未见有“陈皮”或“柑皮”的描述,但新会所在的广南地区已多种柑橘以图利,并掌握了以蚁防治虫害的种植技术。虽然新会种植柑橘在宋元时期未有明确文字记载,但新会所属的广南和南海郡都已经盛产柑橘,新会自然不会例外。另外,据宋末元初诗人刘辰翁凭吊新会“崖山之战”时的赋诗《青玉案(用辛稼轩元夕韵)》:“雪销未尽残梅树。又风送,黄昏雨。长记小红楼畔路。杵歌串串,鼓声叠叠,预赏元宵舞。天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今夜上元何处度。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的描述,宋人有元宵传柑送柑的传统,特别是在王公贵族之间。而“崖山之战”(公元年农历二月初六)发生前20日左右是元宵节,当时的新会还未被元军所占领,根据当时元宵节的习俗,宋军战船上的贵族们应该延续了传柑的传统习惯。所以诗中说“海上传柑”,而柑的来源应是来自于崖山海战宋军驻地新会古井官冲,甚至是新会境内潭江银洲湖流域一带。新会柑冬藏至元宵以及传柑的习俗传统在新会民间仍保留至今。因此可以印证新会在宋末元初种柑已具规模化,并以此图利了。随着元代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元代至正年间,新会人种柑更加普遍,元代至正七年(年)新会龙溪(今江门市江海区外海镇)陈惠甫拨田嘱书中有“甘子田租十石(石读dan与担同音)”记载(有文说此为外海陈族始姐陈莘隐之遗书,据考证非也),这是新会人种柑的最早文字记载。甘,实为柑也,石为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所以一石就是一百升,而担是重量单位,一担等于一百斤,两者单位不同。据前人考证和推算,“甘子田租十石”,是陈惠甫母亲陪嫁的奁田,将其中十亩出租用于种柑,由此可见当时新会柑种植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新会柑种植的首次文字记载)。
三、陈皮功效拓展
3.1陈皮药用历史
由于陈皮因其功效优异得到普遍的认可,元代的本草、方书中已多称作“陈皮”、“真陈皮”了,例如在李东垣(又名李杲)撰《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成书年代不详)、王好古撰《汤液本草》(公元年)、沙图穆苏克撰《瑞竹堂经验方》(公元—年)、吴瑞撰《日用本草》(公元年)、危亦林撰《世医得效方》(公元年)、朱震享撰《本草衍义补遗》(公元年)、王珪撰《泰定养生主论》(公元—年)等均可找到,元末明初伪托唐代孙思邈撰的《银海精微》中有8个药方全部写作“陈皮”,而不写“橘皮”。其中,在李东垣所撰《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一书中,陈皮和青皮开始独立作为一种药材出现,例如著名的六陈歌“枳壳陈皮半夏齐,麻黄野狼毒及茱萸。六般之药宜陈久,入药方知奏奇效”,在平性中记载“青皮快膈除膨胀,且利脾胃”,在五脏补泻主治例中记载“肝虚者,陈皮、干姜之类补之。虚者补期母,肾者肝之母也”,在用药凡例中记载“脐下痛,须用黄柏、青皮……。胸中寒痞,须用去白陈皮……。破滞气须用枳壳、青皮”、“陈皮,味辛苦性温无毒。可升可降,阳中之阴也。其用有二:留白补胃和中;去白消痰泄气”、“青皮,味苦、性寒、无毒。沉也,阴也。其用有四:破滞气愈低而愈效;削坚积愈下而愈良;引诸药至厥阴之分;下饮食入太阴之仓”。在炮制药歌计六首中云“……陈皮专理气、留白补胃中。……何物还须汤泡之,苍术、半夏与陈皮”,在果品部云“陈皮,味辛温无毒,主温脾,青者破积聚”。《汤液本草》亦云:“青皮,气温,味辛。苦而辛,性寒,气厚,阴也。足厥阴经引经药,又入手少阳经。《象》云:主气滞,消食,破积结膈气。去瓤。《心》云:厥阴经引经药也。有滞气则破滞气,无滞气则损真气。《液》云:主气滞,下食,破积结及膈气。或云与陈皮一种。青皮小而未成熟,成熟而大者橘也。色红故名红皮,日久者佳,故名陈皮。如枳实、枳壳一种,实小而青未瓤,壳大而黄紫色已瓤。故壳高而治胸膈,实低而治心下,与陈皮治高、青皮治低同意。又云:陈皮、青皮二种,枳实、枳壳亦有二种。”,书中还记道“能除痰,解酒毒。海藏治酒毒,葛根陈皮茯苓甘草生姜汤。手太阴气逆,上而不下,宜以此顺之。陈皮、白檀为之使。其芳香之气,清奇之味,可以夺橙也”,首次提出陈皮可以解酒毒。《日用本草》中更有“陈皮多年者更妙”;“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消膈气,化痰涎,和脾止嗽,通五淋。”的论述。《世医得效方》·卷第十九·疮肿科·通治:“阿胶饮子:……明阿胶,剉蚌粉炒如珠子,出火毒,一两(缺字),真橘皮半两,粉草一两上剉散。分作三服,水一碗煎,候温,病在上食后服,病在下空心服。累效。”;卷第十·大方脉杂医科·耳病:“立效散:治聤耳、底耳,有脓不止,真陈皮灯上烧黑,一钱,为末,麝香少许,别研右和匀,每用少许,以绵蘸耳内浓净,即上药。”。王珪所撰《泰定养生主论》·卷十六·历用得效方:“大戟圆(出箧中秘宝方,妇人有孕勿服):治一切水气疾蛊,癥瘕食积,大戟(红芽者半两)、巴豆(一百箇去皮,水三升煑干,去心膜出油)、芫花(拣净一两)、甘遂、干姜、真陈皮(去白)、碙砂、姜黄、肉桂(去皮已上各等分)”;“……真陈皮、茴香(微炒)、南木香各半两右为细末”;“茴香(拣净炒)、川练子(去皮核麸炒)、吴茱萸(去仁)、马练花(去蒂梗醋炒)、真陈皮(去白名一两)、芫化(醋炒半两)。”。《本草衍义补遗》云“青皮,苦辛咸,阴中之阳,主气滞,破积滞结气,消食,少阳经下药也。陈皮治高,青皮治低,气虚弱少用,治胁痛须醋炒为佳。”。虽然在宋代已有广皮、真陈皮、真橘皮的多种叫法,但广陈皮的叫法确凿出现在元代汪汝懋所撰《山居四要》(撰于公元—年)·卷五中:“二陈汤:治痰饮为患,呕吐,生冷脾胃不和,伤寒后虚烦上攻,此药最好并宜服之。广陈皮(去白)五钱,半夏(治)五钱,白茯苓(去皮)四钱,甘草右依此。”,由此说明元代的医家已经逐渐认识到陈皮的道地性和广陈皮优越的药效。(这一时期功效延伸至解酒毒、疗疮肿、治耳疾、调理肠胃等,陈皮陈用的观点趋于成熟,开始注重陈皮的道地性)。
3.2陈皮膳用历史
与此同时,在民间饮食实践的基础上,元代宫廷已将陈皮广泛应用于饮膳当中。元代天历三年(公元年)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即首次系统地将陈皮应用于“饮食疗法”。忽思慧主管宫廷饮膳烹调之事,其在任期间,广泛收集蒙、回、维、汉等民族的民间食疗方法,总结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融汇自己为皇家监制饮膳的心得,继承整理古代医学理论的结晶,而撰写出《饮膳正要》。该书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医食同源”、“药食同用”,提倡用饮食营养滋补身体,以达到强身养生的目的,对后世影响和启发很大。《饮膳正要》全书分三卷,卷一讲述诸般禁忌、聚珍异馔等;卷二讲述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其中所列举药膳方都清楚写明疗效,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饮食疗法”记载;卷三讲述料物性味。忽思慧对陈皮药性颇有研究,其在卷三“料物性味”中有陈皮专条记述,评价为“味甘,平。无毒。止消喝,开胃气,下痰,破冷积”,又卷二“食物中毒”有介绍“食鱼脍过多成虫瘕,大黄汁、陈皮末同盐汤服之”、“食鱼中毒,陈皮汁、芦根及大黄、大豆、朴硝汁皆可”等。本书使用陈皮的记载合共有28条,如卷一标明“补中益气”的药膳方“河羹”、“鸡头粉馄饨”、“盏燕”中都有使用陈皮,说明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降气止呕、舒肝利胆、理中和胃、解结化痈等功效;卷二中开列的10款汤、羹、粥品,都有加入陈皮,并说明其疗效。其中汤有5款:茴香汤(治元藏虚弱,脐腹冷痛)、鹿蹄汤(治诸风、虚、腰脚疼痛,不能践地)、狐肉汤(治虚弱、五藏邪气)、乌鸡汤(治虚弱、劳伤、心腹邪气)、鲤鱼汤(治消渴、水肿、黄胆、脚气);羹3款:羊藏羹(治肾虚劳损、骨髓伤败)、羊肉羹(治肾虚衰弱、腰脚无力)、鲫鱼羹(治脾胃虚弱、泄痢,久不瘥者,食之立效);粥2款:羊骨粥(治虚劳、腰膝无力)、猪肾粥(治肾虚劳损、腰膝无力、疼痛)。卷二“食疗诸病”中也有使用陈皮制作的“牛肉脯”,疗效为“治脾胃久冷,不思饮食”。此外,陈皮在发挥药效功用的同时,调味的作用也相当突出,可除肉类腥膻、使之甘醇,令齿颊留香,忽思慧能将陈皮的调味作用发挥到极致,卷一聚珍异馔所列食谱中,使用陈皮的珍稀菜肴有14种,馒头4款(仓馒头、鹿奶肪馒头、茄子馒头、剪花馒头)、包点4款(水晶角儿、酥皮奄子、莳萝角儿、天花包子),使用多要求“各切细”。本人认为,《饮膳正要》一书不但深入研究与饮食有关的医药问题,又是一本古代食谱,其中开列使用陈皮的菜肴、药膳条目较为丰富,由此可见陈皮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已普遍使用,不只是南方,而且在北方也很受欢迎。(食疗广泛应用)。
四、陈皮道地记载
4.1广陈皮道地记载
进入明代,医药界不仅对陈皮的药理、使用方法达成通识,特别注重广陈皮的道地性,而且还发现了陈皮有治妇人乳痈的功效,也第一次提到解鱼腥毒等佐料方面的应用。医院刘文泰等御医于明弘治十八年(公元年)集体撰辑的《本草品汇精要》第三十二卷·果部上品·果之木的橘皮条目下记载的就是:“道地:广东”,由此可以证明明代御医已经完全认可了“陈皮”道地广东,御医们已经开始运用道地的广陈皮为皇室成员治病。在此记载约70多年后,在李时珍于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年至明万历六年(公元年)间编著的《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卷·果之二·橘篇中记述:“今天下多以广中来者为胜,江西者次之”,其中更有详述:“橘皮,苦能泄其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籥,故橘皮为二经气分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陈皮浮而升,入脾肺气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胆气分。一体二用,物理自然也”、“橘皮,入脾、肺二经气分药,疗呕哕反胃嘈杂,时吐清水,痰痞痎疟,大肠秘塞,妇人乳痈。入食料,解鱼腥毒”。在这里,笔者特别注意到明代的医学家不但在皇室,而且在民间临床实践的古方应用过程中,同样注重广陈皮的道地性和特殊效用,并在各自留传的本草方书中记载了详细的使用方法,例如: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所撰的《普济方》中多处出现“广陈皮”、“广橘皮”、“广皮”、“真橘皮”、“陈橘皮”、“陈皮”、“橘皮”。其中卷二百一·霍乱门·霍乱吐利中找到了宋代王璆所辑方书《是斋百一选方》〔又称《百一选方》,是宋代较有影响的方书之一,后经刘承父校正,重新刊刻,内容有增补,名为《新刊续添是斋百一选方》(公元年),流传过程中逐渐佚散了,但仍为后世医家所引〕中“回生散”的方子:“治霍乱吐泻,但一点胃气存者,服之无不回生。陈皮(去白)、藿香叶去土,右等分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至七分,温服不拘时。”,到了李时珍所在时期,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同样援引了“回生散”的方子:“霍乱吐泻,不拘男女,但有一点胃气存者服之再生,广陈皮(去白)五钱、真藿香五钱,水二盏煎一盏时时温服(出自)。”。在差不多与李时珍同时代的明代名医缪希雍(公元年)在《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三·果部三品中亦引用了同样的方子:“霍乱吐泻,但有一点胃气存者服之即生,广陈皮(去白)五钱,真藿香五钱,水二盏煎一盏,时时温服食疗治。”。秦景明(—年)撰《症因脉治》·卷四·异功散:“白术、人参、真广皮、炙甘草、白茯苓。”。由此可以印证李时珍、缪希雍、秦景明等人在实际临床过程中,通过各地出产陈皮的药性对比,得出陈皮以广东产为最好的结论,并且都对前人的方子作了修改,采用了道地的广陈皮入药,足可见他们对广陈皮药效的推崇。而明代黄一龙所修广东《潮阳县志》·卷十二·物产一篇中亦有记载:“陈皮即广陈皮,产于此者特佳。”,可见广陈皮这个叫法在明代相当普遍,说明广陈皮不仅药效好,而且广橘皮及广陈皮的生产已经有相当大规模,以致响誉全国。(这一时期增加治妇人乳痈的功效,更加注重广陈皮的道地性)。
而关于陈皮以“陈久者良”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已渐趋成熟。例如前述《本草品汇精要》称“至十月霜降后已成熟者,味辛而黄大谓之橘皮,医家所用陈皮即经久者是也”。贺岳于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年)所撰《本草要略》云“陈皮隔年者方可用”;陈嘉谟于明嘉靖四十四年(即公元年)编著的《本草蒙筌》言“久藏者名陈皮,气味辛烈,痰实气壅服妙”、“青皮、陈皮……因其迟早采收,特分老嫩而立名也。嫩者性酷治下……老者性缓治高”、“新采者名橘红,气味稍缓,胃虚气弱者宜;久藏者名陈皮,气味辛烈,痰实气壅服妙。东垣又曰:留白则补胃和中,去白则消痰利滞。治虽分二,用不宜单。君白术则益脾,单则损脾;佐甘草则补肺,否则泻肺。同竹茹,治呃逆因热;同干姜,治呃逆因寒,止脚气冲心,除膀胱留热。利小水,通五淋,解酒毒,去寸白;核研仁调醇酒饮,驱腰痛疝痛神丹;叶引经以肝气行,散乳痈胁痈圣药;橘囊上筋膜微炒,醉呕吐发渴急煎。谟按:青皮、陈皮一种,枳实、枳壳一种,因其退早采收,特分老嫩而立名也。嫩者性酷治下,青皮枳实相同;老者性缓治高,陈皮枳壳无异。四药主治并以导滞消痞为专,虽高下各行,其泻行则一。单服久服俱损真元,故必以甘补之药为君,少加辅佐,使补中兼泻,泻则兼补,庶几不致于偏胜也。陈皮款下已详发明,余虽未言,举一隅则可以三隅反矣。”。杜文燮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年)编撰《药鉴》在“六陈药性”中提到“陈皮须用隔年陈”,又称陈皮“必须年久者为美”。在李中梓于明天启二年(公元年)编撰的《删补颐生微论》·卷三·药性论第二十一·果部载:“橘皮:味辛性,微温,无毒。入肺脾二经。产广中者良,陈久者良。去蒂及膜用,开胃健脾,消痰理气,止嗽定呕,消食开郁。”,其另一部更加出名的著作《雷公炮制药性解》则记载“去白者兼能除寒发表,留白者兼能补胃和中。微炒用。产广中,陈久者良。按:陈皮辛苦之性,能泄肺部金,金能制水,故入肝家,土不受侮,故入脾胃。采时性已极热,如人至老成,则酷性渐减。收藏又复陈久,则多历梅夏而烈气全消。温中而无燥热之患,行气而无峻削之虞,中州之胜剂也。乃《大全》以为多用,独用有损脾胃,师心之过耳。”,这里首次提出道地产区为广中(即现珠三角一带)以及“陈久者良”的明确说法并解释了原因,李中梓根据中医论治理论深刻的分析了广陈皮药效优势,指出广陈皮具有“温中而无燥热之患,行气而无峻削之虞”的重要特点。倪朱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年)编撰《本草汇言》云“又他药贵新,惟橘皮贵陈”、“今以广中者称胜。素华,丹实。皮既馨香,又有善味”、“味辛善散,故能开气;味苦开泄,故能行痰;其气温平,善于通达,故能止呕、止咳,健脾和胃者也。东垣曰:夫人以脾胃为主,而治病以调气为先,如欲调气健脾者,橘皮之功居其首焉。”。卢之颐于明崇祯七年前后(公元年)编撰的《本草乘雅半偈》·卷三·本经上品五·橘柚:“本经上品橘柚,气味辛温,平,无毒。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覈曰:橘柚生江南,及山南山谷。今以广中者称胜。素华,丹实。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专胜在皮,虽年深日久,不但芳辛不改,转更清烈”、“观又不如佛肚脐形小皮癞甘美可口也。霜降采,取气足味。足密藏至春,剖皮抽脉破囊吮汁,亦可振精醒神。为得句破疑之助,若欲择皮用充药饵,不若广中者皮薄而香愈陈,则愈善也。”,卢之颐对广陈皮认识比较全面,不仅说明了广陈皮道地,还详细描写了广陈皮的性状和药效特点“皮薄而香愈陈,则愈善也”,指出皮薄而香和老陈是广陈皮的重要特性。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缪希雍在其所撰《先醒斋广笔记》·卷四·橘皮中首次明确真广陈皮的辨别和使用方法:“真广陈皮,猪鬃纹,香气异常,去白时不可浸于水中,止以滚汤手蘸三次,轻轻刮去白要极净。”,“真”、“广”、“陈”三字不仅高度概括了道地性,还明确了陈久者良,而“猪鬃纹”、“香气异常”则是道地性和陈久的辨识特征。(陈久者良以及真陈皮的辨识特征)
虽然在宋代已有青皮入药的记载,但直至明代,各类本草才进一步阐明了青皮的性味和功效,并提出了慎用的观点。例如明初徐彦纯撰《本草发挥》载:“洁古云:青橘皮气温味辛。主气滞,下食破积,结膈气,及小腹痛。《主治秘诀》云:性寒味苦,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其用有五:足厥阴、少阳之分,有病则用之,一也;破坚癖,二也;散滞气,三也;去下焦湿,四也;治左肾有积气,五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亦有论述“青皮乃橘之末黄而青色者,薄而光,其气芳烈。古无用者,至宋时医始用。其色青气烈,味苦而辛,治之以醋,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酸泄之,以苦降之也。陈皮浮而升,入脾、肺气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胆气分。一体二用,物理自然也。小儿消积多用青皮,最能发汗,有汗者不可用,出自杨仁斋《直指方》,人罕知之。治胸膈气逆,胁痛,小腹疝气,消乳肿,疏肝胆,泻肺气。”。同一时期,陈嘉谟在其编著的《本草蒙筌》亦言“青皮,味辛、苦,气寒。味厚,沉也,阴也,阴中之阳。无毒。《汤液》云:陈皮治高,青皮治低,亦以功力大小不同故尔。入少阳三焦胆腑,又厥阴肝脏引经。削坚癖小腹中,温疟热盛者莫缺;患疟热盛,缠久不愈,必结癖块,俗云疟母。宜清脾汤多服,内有青皮疏利肝邪,则癖自不结也。破滞气左胁下,郁怒痛甚者须投。劫疝疏肝,消食宽胃。病已切勿过服,恐损真气,先防老弱虚羸,尤当全戒”。其后,杜文燮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年)在其所编撰的《药鉴》述“青皮,气寒,味苦辛,气味俱厚,无毒,沉也,阴也。足厥阴引药也。破滞气,愈低而愈效。削坚积,愈下而愈良。引诸药至厥阴之分,下饮食入太阴之仓。又少阴经下药也。陈皮治高气,青皮治低气。佐柴胡,能治两胁刺痛,醋炒为佳。君芍药,又伏胆家动火,胆制为良。劫疝疏肝,消食宽胃。惊家诸药,用一二分为妙。”。而李中梓于明天启二年(公元年)编撰的《删补颐生微论》·卷三·药性论第二十一·果部载“青皮,味苦酸,性温,无毒,入肝、脾二经。主破滞气,愈低而愈效。削坚积,愈下而愈良。引诸药至厥阴之分,下饮食入太阴之仓。消温疟热甚结母,止左胁郁怒作疼。按:青皮即橘之小者,酸能泻木,宜走肝经;温能消导,宜归脾部。其性峻削,多服伤脾,虚羸禁用。”。张景岳于明天启四年(公元年)编撰《景岳全书》“青皮,味苦辛微酸,味厚,沉也,阴中之阳。苦能去滞,酸能入肝,又入少阳、三焦、胆腑。削坚癖,除胁痛,解郁怒,劫疝疏肝,破滞气,宽胸消食。老弱虚羸,戒之勿用。”。缪希雍于明天启五年(公元年)在《神农本草经疏》·卷二十三·果部三品中进一步阐述了青皮的药性和指明慎用的原因:“青皮古方无用者,至宋时医家始用之。其色青,其味极苦而辛,其气温而无毒。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入足厥阴、少阳。苦泄,辛散,性复刻削,所以主气滞,下食,破结积及膈气也。元素:破坚癖,散滞气,治左胁肝经积气。亦此意耳。简误:青皮性最酷烈,削坚破滞是其所长。然误服之,立损人真气,为害不浅。凡欲使用,必与人参、术、芍药等补脾药同用,庶免遗患,必不可单行也。肝脾气虚者,概勿施用。”。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青皮性削,行肝胆经,主要用于破坚去癖、宣泻肺气、解郁去怒、劫疝疏肝、消食宽胃、消除乳肿、下焦去湿等,但应与人参、柴胡、白术、芍药等补脾药同用,且勿过服。肝脾气虚、有汗者以及老弱虚羸应禁用。(青皮慎用)
4.2新会陈皮道地记载
新会种柑取皮的历史记载最出名莫过于明代大儒陈献章在其诗歌中的描述。陈献章(公元—年)字公甫,广东新会人。因曾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世称为陈白沙。他在《陈白沙集》中有若干首诗描写了家乡新会的柑橘,例如卷八·古风歌行·《题马默斋壁》“屋后青山屏翳合,簷前绿树烟花匝。主人闭门履不纳,跏趺明月光遶榻。客来问我笑不答,但闻山莺啼恰恰。橙橘盈园野芳杂,门外一江深映合。四时八风谁管押,烟飞雾走龙腾甲。拙者孤舟持酒榼,成化十年甲午腊。”,这首诗写于明成化十年,描写了橙橘盈园的生机景象;卷六·七言绝句·《送柑答之》“遗我红柑索我歌,狂柑不饮奈柑何。大崖山下无人寄,日尽千瓢舞破蓑。〔大崖世卿读书处也〕。”,这首诗是陈献章在新会崖门大崖山凭吊古战场写的,这里曾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宋元两军“崖山之战”。诗题为《送柑答之》,诗中提到的红柑就是新会著名的大红柑,新会皮便是大红柑取皮晒制而成;又《陈白沙集》·卷八·七言律诗·《玄真送柑》:“溪园十月摘黄柑,岁月将穷致小篮。绕膝痴孙高起舞,隔年乳酒正开坛。色香本出梨之右,风味真无岭以南。不惜霜根传药圃,白头还解荷长镵。”,这首诗描写了新会十月摘柑的情景。直至现在,新会亦是在农历十月左右摘柑。“不惜霜根传药圃”一句,则充分说明新会在明代已有专门药用的柑园。将该诗文与《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六·列传十五(明新会)·明:“新会采药者不知何许人,日采九里明卖以为食,其药多生柑、荔圃。旦暮入采之,绝不视柑、荔,虽自落亦不顾。”的记载相互印证,因此,可以确定新会柑在明代已经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果园种植了,所产广陈皮已崭露头角,并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明代新会柑种植以及取皮入药的文字记载)
到了清朝时期,张志聪及其弟子高世栻于康熙十三年(公元年)撰《本草崇原》,其述:“橘皮,气味苦、辛、温,无毒。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青橘皮,气味苦,辛,温,无毒。主治气滞,下食,破积结及膈气”。陈士铎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年)撰《本草新编》(又名本草秘录),其详细分析了陈皮和青皮的不同功效并指明具体的使用方法:“橘皮,味辛、苦,气温,沉也,阴中之阳,无毒。陈皮治高,青皮治低,亦以功力大小不同也。入少阳三焦、胆腑,又入厥阴肝脏、太阴脾脏。青皮,消坚辟,消瘟疟滞气,尤胁下郁怒痛甚者须投,却疝疏肝,消食宽胃。橘红名陈皮,气味相同,而功用少缓,和中消痰,宽胁利膈,用之补,则佐补以健脾;用之攻,则尚攻以损肺。宜于补药同行,忌于攻剂共用。倘欲一味出奇,未有不倒戈而自败者也。或问陈皮留白为补,去白为攻,然乎?此齐东之语也。陈皮与青皮,同为消痰利气之药,但青皮味厚于陈皮,不可谓陈皮是补而青皮是泻也。”、“或问陈皮即橘红也,子何以取陈皮而不取橘红?夫陈皮之妙,全在用白,用白则宽中消,若去白而用红,与青皮何异哉。此世所以“留白为补,去白为攻”之误也。其实,留白非补,和解则有之耳。”、“或问世人竟尚法制陈皮,不知吾子亦有奇方否?曰:陈皮制之得法,实可消痰,兼生津液,更能顺气以化饮食。市上贸易者非佳,惟姑苏(经考证并非指产于姑苏,而是实指广陈皮中产于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的三级苏红皮。关于陈皮的级别和分类,另文介绍)尤胜。然又过于多制,惟取生津,而不能顺气。余有方更妙,用陈皮一斤,切,不可去白,清水净洗,去其陈秽即取起。用生姜一两,煎汤一碗,拌陈皮晒干。又用甘草、薄荷一两三钱,煎汤,拌陈皮,又晒干,又蒸熟晒干。又用五味子三钱、百合一两,煎汤二碗,拌匀又蒸晒。又用青盐五钱、白矾二钱,滚水半碗拌匀,又蒸熟晒干。又用人参三钱,煎汤二碗,拌匀蒸熟晒干。又用麦门冬、橄榄各一两煎汤,照前晒干,收藏于磁器内(九制陈皮之方?)。此方含在口中,津液自生,饮食自化,气自平而痰自消,咳嗽顿除矣。修合时,切忌行经妇人矣。”、“或问陈皮用之于补中益气汤中,前人虽有发明,然非定论,不识先生之可发其奇否?夫补中益气汤中用陈皮也,实有妙义,非取其能宽中也。气陷至阴,得升麻、柴胡以提之矣。然提出于至阴之上,而参、芪、归、术,未免尽助其阳,而反不能遽受。得陈皮,以分消于其间,则补不绝补,而气转得益。东垣以益气名汤者,谓陈皮而非谓参、芪、归、术也。”。汪昂(字讱庵)于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年)在《本草备要》中提到:“广中陈久者良,故名陈皮,陈则烈气消,无燥散之患。半夏亦然,故同用名二陈汤。治痰咳,童便浸晒。治痰积,姜汁炒。治下焦,盐水炒。去核、皮、炒用。”、“青皮,泻肝,破气,散积。辛苦而温,色青气烈。入肝胆气分。疏肝泻肺,柴胡疏上焦肝气,青皮平下焦肝气。凡泻气药,皆云泻肺。破滞削坚,除痰消痞。治肝气郁积,胁痛多怒,久疟结癖,入肝散邪,入脾除痰,疟家必用之品,故清脾饮以之为君。疝痛乳肿,丹溪曰:乳房属阳明,乳头属厥阴。乳母或因忿怒郁闷,厚味酿积,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出;阳明之血腾沸,故热甚而化脓。亦有其子有滞痰膈热,含乳而睡,嘘气致生结核者。初起便须忍能揉软,吮令汁透,自可消散。治法以青皮疏肝滞,石膏清里热,甘草节行浊血,瓜蒌消肿导毒,或加没药、橘叶、金银花、蒲公英、皂角刺、当归,佐以少酒,若于肿处灸三五壮尤捷。久则凹陷名乳岩,不可治矣。最能发汗,皮能达皮,辛善发散。有汗及气虚人禁用。陈皮升浮,入脾肺治高;青皮沉降,入肝胆治低。炒之以醋,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酸泄之,以苦降之也。橘之青而未黄者,醋炒用。古方无用者,宋以后始与陈皮分用。”,此外,其撰写的《本草易读》亦述“色红陈久者佳。去白为橘红。去白消痰,留白和中。苦,辛,温,无毒。化痰治嗽,顺气理中,调脾快膈,止呕降冲,利水消谷,通淋润肠。疗霍乱吐泻,除嘈杂吐青;破症瘕癖,解鱼腥肉腐。入食料最宜,杀寸白亦良。橘皮细纹红色,皮薄而多筋,其味苦辛。若纹粗色黄皮浓,内多白膜无筋,味甘辛者,柑皮也。纹极粗色黄,内多膜无筋,皮极浓,味甘多辛少者,柚皮也。今天下多以柑皮杂之,柑皮犹可,柚皮则悬绝矣。去净内白名橘红,专于消痰下气。生江南。十月采。嘈杂吐水,真橘皮为末,五更安五分掌内,以舌舐之,即睡,三日必效。(验方第一。);霍乱吐泻,但有一点胃气存者,服之再生。真橘皮五钱,真藿香五钱,时时煎服。(第二。);反胃吐食,真橘红,西壁土炒,同姜枣煎服。(第三。);猝然噎食,炒末煎服。(第四。);痰膈气胀,水煎服。(第五。);积年气嗽,同神曲、生姜蒸饼丸服。(第六。);脚气冲心,心下结硬,佐杏仁蜜丸服。(第七。);老人气秘。同上。(第八。);风痰麻木,湿痰死血为患也。橘红一斤,水煎烂,去渣再煎,顿服取吐。(第九。)。润下丸橘皮(半斤,盐水淹过煮干)、炙草(二两),蒸丸豆大,每百丸。治痰停胸膈,咳唾稠粘。(诸方第一。)。宽中丸陈皮(四两)、白术(二两),酒丸服。治胀满壅塞不通。(第二。)。二贤散橘红(一斤,陈皮亦可)、甘草(四两)、食盐(五钱)水煮烂,晒干为末,白汤下。治积块,进饮食。有块加姜黄,气滞加香附,噤口加莲肉。”、“青皮去瓤醋炒用。苦,辛,温,无毒。入肝胆经。下滞气而消食,破坚癖而祛胀;治两胁之郁痛,降胸膈之气泻肺气而平乳痈。乃橘之未黄而青色者,薄而光,其气芳烈。今人多以小柑、小柚、小橙伪为之,不可不知。”。清代著名医家张璐在康熙三十四年(公元年)所著《本经逢原》·卷三·果部·橘皮目载:“橘皮苦辛温,无毒。产粤东新会,陈久者良。阴虚干咳,蜜水制用。”、“青皮古方所无,至宋时医家乃用之。入足太阴、厥阴,破滞气,削坚积,及小腹疝疼,用之以疏通二经,行其气也,小儿消积多用之。青皮最能发汗,多汗者勿用。久疟热甚,必结癖块,宜多服清脾饮,内有青皮疏利肝邪,则癖自不结也。中气虚人禁用,以其伐肝太甚,而伤生发之气也。”,其首次明确提出以新会产的陈皮为佳,后代医家亦大多持此相同看法,新会陈皮在清代是被医家盛行使用的高峰,新会陈皮自此有了自己的道地称呼“新会皮”。新会皮的称呼至此始于何时何人,大致也可以找到了答案。经考证,新会皮的称呼几乎没有出现在明代任何本草著作中,而是首先出现在清代的医案中,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清代康乾年间大医士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和与叶天士齐名的薛雪的《扫叶庄医案》,二人同时代且是同乡名医。二人医案中陈皮多用“新会皮”、“会皮”,这大概得传于叶天士的老师苏州名医王子接。王子接弟子叶天士、吴蒙整理了老师的《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年),王子接在他的《绛雪园古方选注》中喜欢使用“广陈皮”、“广皮”,在叶天士等人著作的影响下,新会皮被很多清代医学家认可,使用新会皮的其他清代医学著作有《增广大生要旨》、《医方丛话》、《串雅》、《爱月庐医案》等。而吴仪洛于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年)在《本草从新》中再次阐述了陈皮“陈久者良”的观点:“橘皮,如人至老年,烈性渐减,经久而为陈皮,则多历寒暑,而躁气全消也。”。前段时间热播的古装剧《延禧攻略》中出现的清代御医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南阳先生)所著《本草经解》述:“陈皮,气温.味苦辛,无毒。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陈皮气温,禀天春升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味苦辛无毒。得地南西火金之味,入手少阴心经、手太阴肺经,气味升多于降,阳也。胸中者肺之分也,肺主气,气常则顺,气变则滞,滞则一切有形血食痰涎,皆假滞气而成瘕,瘕成则肺气不降而热生焉,陈皮辛能散,苦能泄,可以破瘕清热也,苦辛降气,又主逆气,饮食入胃,散精于肝,温辛疏散,肝能散精,水谷自下也,肺主降,苦辛下泄,则肺金行下降之令,而下焦臭浊之气,无由上升,所以去臭而下气也。心为君主,神明出焉,味苦清心,味辛能通,所以通神也。:陈皮留白和中,去白消痰理气,同术补脾,同甘草补肺,同补气药补气,同破气药破气,同消痰药去痰,同消食药化食,各从其类以为用也。同人参、首乌、桂枝、归身、姜皮,治三日疟寒多;同白蔻、生姜、藿香、半夏,治寒痰;同白茯、甘草、半夏,名二陈汤,治痰症;同生姜,治哕;同藿香.治霍乱吐泻;同姜汁焙末,同枣煎,治脾疟;去白为末,麝香调酒下,治乳痈初发;盐汤泡,刮去白,同甘草丸,治痰涎上泛;同白术丸,名宽中丸,治脾虚胀满,不思饮食。”;“青皮气温,味辛苦,无毒,主气,下食,破积结,及膈气。青皮气温,禀天春和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味辛苦无毒,得地西南金火之味,入手太阴肺经、手少阴心经,气味升多于降,阳也。其主气者,味辛入肺,肺主气,而辛温能通也。下食者,饮食入胃,散精于肝,气温入肝,肝能散精,食自下也,辛能散,温能行,积者破而结者解矣。肝主升,肺主降,升而不降,气膈于右,降而不升,气膈于左,温可达肝,辛苦泄肺,则升降如而膈气平矣。青皮同人参、鳖甲,治疟母;同枳壳、肉桂、川芎,治左胁胀满痛。”。严洁、施雯、洪炜于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年)同纂《得配本草》述“橘皮即黄橘皮,一名红皮,年久者曰陈皮。产广中者曰广皮,尤良。辛、苦,温。入手足太阴经气分。导滞消痰,调中快膈,运胃气,利水谷。止呕逆,通五淋,除膀胱留热,去寸白虫蛊。解鱼腥毒。得川连、猪胆,治小儿疳瘦;得麝香,治乳痈(研末酒下);配干姜,治寒呃;配竹茹,治热呃;配白术,补脾;配人参,补肺;配花粉,治咳嗽;配炙甘草、盐,治痰气;配藿香,治霍乱;配槟榔,治气胀;佐桃仁,治大肠血秘;佐杏仁,治大肠气秘;合生姜、半夏,治呕哕厥冷。去白名橘红,消痰下气,发表邪,理肺经血分之郁。留白和中气,理脾胃气分之滞。治痰,姜汁炒。下气,童便炒。理下焦,盐水炒。虚人气滞,生甘草、乌梅汁煮炒。汗家,血家,痘疹灌浆时,俱禁用。”、“青皮,辛、苦、温。入足厥阴、少阳经气分。破坚癖,散滞气,消积食,除疝瘕。柴胡疏上焦肝气,青皮理下焦肝气。配浓朴、槟榔,达膜原之邪;配枳壳、肉桂,治胁痛;佐人参、鳖甲,消疟母;和酒服,治乳内结核。橘未黄而青色者。醋炒黑用,能入血分。最能发汗,(皮能达表,辛能发散。)气虚及有汗者禁用。”。叶桂门生华岫云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年)搜集其医案编写的《临证指南医案(十卷)》所开“二陈汤”就特别指明用“新会皮”,该书开列方剂中有写明采用“新会皮”的有25个处方。许豫和于乾隆五十年(公元年)撰《怡堂散记》“(陈皮)新者气烈,须备广产,二三年者为上”。由此可知,古人认为陈皮久置可减少因辛燥之性而至的耗气之弊。黄宫绣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年)撰《本草求真》曰“[批]宣肺气燥脾湿,橘皮(专入脾肺。兼入大肠)。味辛而温。治虽专主脾肺。(时珍曰。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签。故橘皮为二经气分药。)调中快膈。导痰消滞。利水破症。宣五脏理气燥湿。(汪自曰。大法治痰以健脾顺气为主。洁古曰。陈皮枳壳利其气而痰目下。)然同补剂则补。同泻剂则泻。同升剂则升。同降剂则降。各随所配而得其宜。(凡补药涩药。必佐陈皮以利气。)且同生姜。则能止呕。(十剂篇云。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是也。)同半夏则豁痰。同杏仁则治大肠气闭。同桃仁则治大肠血闭。至其利气。虽有类于青皮。但此气味辛温。则入脾肺而宣壅。不如青皮专入肝疏泄。而无入脾燥湿。入肺理气之故也。(诸湿皆属于脾。诸气皆属于肺。)然多服亦能损气。(胃气亦赖痰养。不可用此尽攻。)用补留白。下气消痰除白。(出圣济)即书所名橘红。(今人有以色红形小如枳实者代充。其破气实甚。)然亦寓有发表之意(以皮治皮意)。核治疝痛偏坠(凡核多入肾。而橘核尤入囊核。亦物类相感意。时珍曰。橘核入足厥阴肝,与青皮同功。故治腰痛疝痛。及内卵肿偏坠。或硬如石。或肿至溃。有极核丸。用之有效。)、叶散痈肿(莫强中为丰城令时得疾。凡食已。辄胸满不下。百方不效。偶家人合橘红汤。因取尝之。似相宜。连日饮之。一日。忽觉胸中有物坠下。大惊目瞪。自汗如雨。须臾腹痛。下数块如铁弹子。臭不可闻。自此胸次廓然。其疾顿愈。盖脾之冷积也。其方用橘皮一斤去穣。甘草盐花各四两。为末。煮干点服。名二肾散。丹溪变为润下丸。用治痰气有效。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取广陈久者良(陈则烈气消散,故名陈皮,与半夏同用,名为二陈。);治火痰童便制;寒痰姜汁制;治下焦盐水制。核去皮炒用。”、“[批]行肝气滞。青皮专入肝。本于橘生,其皮则一,何为因青而异。盖犹人当少壮,则性躁暴而少柔,人当老年,则性渐减而不躁。青皮未经寒暑,燥气不消,故其赋性最劣,其色青,青属木,木主肝,故青独于肝经则入。其味苦,故能入肝而下气。杲曰:青皮乃足厥阴引经之药,能引食入太阴之仓,破滞削坚,皆治在下之病。然仍兼有辛气内存,故于下中仍兼宣泄。柴胡疏上焦肝气,青皮平下焦肝气,陈皮浮而上入脾肺气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胆气分,气味各别如此。是以书载力能发汗,时珍曰:小儿消积,多用青皮,最能发汗。破泄削坚,除痰消痞,并气郁久怒,久疟结癖,嘉谟曰:久疟热甚,必结癖块,宜多服青皮汤,内有青皮疏利肝邪,则癖自不结也。疝痛,疝痛有由足厥阴郁气。乳肿,丹溪曰:乳房属阳明,乳头属乳阴,乳母或因忿怒郁闷,厚味酿积,致厥阴之气不行,故窍不得开,阳明之血腾沸,故热甚而化脓,亦有其子有滞痰膈热,含乳而摇嘘气,致生结核者,初起便须忍痛揉软,吮令汗透,自可消散,治法以青皮疏肝滞,石膏清胃热,甘草节行浊血,栝蒌消肿导毒,或加没药、橘叶、金银花、蒲公英、皂角,少酒,若于肿处灸三五壮尤佳。久则凹陷,名乳岩,不可治矣。无不奏效,但有汗气虚切忌。时珍曰:有滞气则破滞气,无滞气则损真气。”。杨时泰于道光十三年(公元年)撰《本草述钩元》·卷十七·山果部·陈橘皮:“陈橘皮:〔修治〕入和中理胃药则留白,入下气消痰药则去白,去白者以盐汤洗浸。刮去筋膜,晒干用。自广州来陈久者佳,真广陈皮,猪鬃纹,香气异常,去白时不可浸于水中止,以滚汤手蘸三次,轻轻刮浄,人下焦须用盐水浸,肺燥则用童便浸晒。”,强调了“真广陈皮”以及“自广州陈久者佳,真广陈皮,猪鬃纹,香气异常”,不仅用“真”字强调广陈皮的道地和“香气异常”,还描述了“真广陈皮”制作方法和用法。凌奂于咸丰年间所著《本草害利》“广东新会皮为胜,陈久者良,故名陈皮。福建产者名建皮,力薄。浙江衢州出者名衢皮,更次矣”。其记载的道地产区与今完全吻合。其后,道光年进士陆以湉在其所著《冷庐杂识》·卷二·饧中描述:“余谓:今之庸医,不特未识古方也,即寻常药品,亦不能辨其名。有书‘新会皮’作‘会皮’,盖不知新会是地名也。”,清代宫廷御医很多会在开完药方后,注明中药的产地,在广陈皮下注:“产广东,以新会县署内者最佳。”,新会皮作为御用道地药材,为清室服务深得御医和皇家的肯定。此外,清代医学界还发现了陈皮的燥湿之功,并提出了可以去郁,相关的记载有姚澜(又名维摩和尚)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年)撰《本草分经》:“广陈皮,辛、苦、温。入脾、肺气分,能散、能和、能燥、能泻。利气调中,消痰快膈,宣通五脏,统治百病”、“青皮,辛、苦,温。沉降气烈。入肝胆气分。疏肝泻肺,破积消痰,最能发汗。引诸药至厥阴之分。兼入脾,下饮食。”。(清代对陈皮和青皮功效的理解更深,名医们广泛使用陈皮于汤剂和丸散)。
关于新会柑种植和陈皮的地方史志记载有清乾隆年间撰修的《新会县志》·卷六:“馀甘俗名油柑,苹浦女药之属,陈皮邑出者佳。”,这是《新会县志》第一次夸赞本县陈皮,在此亦能看到新会柑品种细分的端倪,这里的油柑应该就是特指相对于大红柑的大种油身柑或者油身仔了。清咸丰陈淑均纂台湾府《噶玛兰厅志》记:“陈皮、橘皮也以广中陈久者良,能燥能宣有补有泻,可升可降。”这说明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在清代也知道广陈皮的道地和药效,普世广泛应用,可见广陈皮的知名度和广陈皮所销范围之远。道光版《新会县志》·卷二·物产载:“柑树如橙,花叶畧小,味酢,冬至后味转甜,劈其皮香雾噀人,暴乾生而青者名青皮,熟而红者名大红皮,凡果之皮以柑皮为尤佳,故又名果皮。入药去白用能除痰,与橘红同功,陈者良。取红柑压扁去核,白糖煮之,名曰柑饼,味绝佳,胜於橙。种植者千百株成围,每岁大贾(缺一字)其皮售於他省,绕过岭北,其香转胜,其利最溥,四五月落实不堪食,暴乾为线香料。约二十年树老,斫之为薪,久而不盡,其灰可拭铜锡物,去腻生光,能洗字,果中之全材也。”,这里提到的大红皮应为大红柑(与油柑相区别)所取之皮,县志再次夸赞其可入药除痰,陈者为佳。而县志中所载“其扇有长柄、二旗、三旗、玻璃等名,长柄者,其树尚穉媆,其长柄至数尺,柄之皮甚靭,斯而为藤,绾扇之边复加大小二竹以合之,其小竹如丝名曰合仔(按邑城东门外数里有村梁姓专门以合仔为业,人称合仔梁)俗名草边是也,柄次皮可为绳,绳以缚陈皮为往外省。”,则说明了当时新会本地人(合仔梁,位于现江门市新会区灵镇一带)已有保护品牌的意识,懂得利用当地另一种特产蒲葵的葵柄外皮搓成俗称“牛绳”的细绳用于捆缚包装新会陈皮销往外省,作为新会陈皮地道、防伪的标志。清末光绪三十四年(年)《新会乡土志》·九·实业:“新会自前明江门学派既兴,邑士著录白沙门下者,县志所载,犹得七十余人,师友渊源,儒风赓续。县境当西江下流,膏腴弥望,农业尤称盛焉,物产如橙柑蒲葵之类,皆此土特色,挟资本以输运於外埠者,接轸连辖,亦泱泱商国也。……全境农民,约占半数,农类以种稻为普通之业,而近城参植蒲葵柑蔗……商务·邑城内外,多业蒲葵果皮,其设肆本境及贩运外埠者,可二百家。”;十四·物产·(乙)植物:“柑皮之独可入药,为他地所不及,则尤其特别者也……柑拟橙而大,身扁,皮可为药,名曰陈皮,盖以陈久为贵为。其肉甘香,不亚于橙,惟遇风雨则多落,遇霜雾则多腐,农户业此者,每当飓风淫雨之年,大受耗损,且果不耐久,难於远销,树身又不长寿,於农业经济,不甚相适也。邑中果园,业此最为大宗,然皆在县境南部,他部则虽有亦少,以东甲为尤多,南坦为尤良。”;(丁)制造品·植物制造:“陈皮可作药料,为柑果之皮曝干者,岭北人甚重之,盖经北方霜雪地,香倍於常也,他邑所产者不如也。线香用檀麝及青柑皮等粉末和胶制成,燃之有馥郁之气,销行甚多,江门多业之”;九·商务·输出品·生果:“每年出口约值银一百万元,行销香港省城陈村佛山等处,以柑果为最多,桔次之。”,更进一步说新会陈皮是当地特产,集中于县境南部种植,他部则虽有亦少,以东甲为尤多,南坦为尤良比其他地方的陈皮好,具有道地性。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新会柑种植和陈皮生产、贸易达到了建国前的高峰。张寿颐于年在其所著《本草正义》言:“其通用者,则新会所产,故通称曰新会皮。”。陈仁山于年编著的《药物出产辨》也说:“陈皮产广东新会为最,四会、潮州、四川所产者,俱不适用。以十一月冬至前后收者为合宜。《万国药方》卷三·一百零九篇,论西药呼之为橘皮,实考究不真。陈者旧也,俗名果皮之称,焉能乱忙改其名为橘皮?大橘皮另有一种,岂可混合而言耶!是西医未能分辨清楚,妄登医本耳。陈皮之名称最多、最好者,头红皮,第二大红皮,第三极红皮,第四苏红皮,第五二红皮,第六简红皮,第七旱水皮,第八青皮。主治:辛、甘,下气开中。(藏器)”、“青皮产广东新会。主治:苦、辛,温。破坚癖,散气滞,治左胁肝经积气。(元素)”。直至今天新会皮出产于广东新会,依然是全国闻名通用的保健佳品和药材。
通过对上述文献记述进行对比分析,陈皮的功用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橘柚,味辛,温。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主要涉及到理气健脾消食的功用。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又增加了止咳,利尿止淋等功用,原文为“主下气,止呕咳,治气冲胸中,吐逆霍乱,疗脾不能消谷,止泻,除膀胱留热停水,五淋,利小便,去寸白。久服轻身长年。”,其后的本草著作开始对陈皮的理气,止咳化痰的功效进行了总结。如隋唐时期的《本草拾遗》:“能去气调中”;《药性论》:“清痰涎,开胃治上气咳嗽,主气痢,破癥瘕痃癖,治胸膈间气。”;《日华子本草》:“消痰止咳,破癥瘕痃癖”;《珍珠囊》:“利肺气”。可以说随着历代医家的临床验证,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逐步确定。宋元时期,本草药典又记述了陈皮具有祛痰驱寒、解酒毒、疗疮肿、治耳疾、调理肠胃的功效以及食疗的具体应用。如:《汤液本草》“能除痰,解酒毒。海藏治酒毒,葛根陈皮茯苓甘草生姜汤”;《世医得效方》记述了利用陈皮疗疮肿、治耳疾的药方等。到了明清时期,本草学家和医家对本草功用认识更加深入,而且进行了高度总结,陈皮的功效得以最终确定。如《本草备要》:“调中快膈,导滞消痰,……皆取其理气燥湿之功。”;《本草分经》:“能散能和,能燥能泻,利气调中,消痰快膈,宣通五脏,统治百病”,这此认识与现代药典记述陈皮的“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功用已经基本一致。陈皮能治百病是因为其辛能散温能和,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随所配而补泻升降,温而不燥,其主要功效有:①化痰止咳(消痰涎、治上气咳嗽、消痰止嗽、痰实结气、消痰泄气);②理气宽胸(胸中瘕热逆气、气冲胸中、胸膈间气、胸中滞气、快膈、理气);③降逆止呕(逆气、下气、呕吐、胸中吐逆);④健胃消食(开胃、脾不能消谷、补胃和中、调中、导滞、燥湿);⑤止泄止痢(霍乱、止泄、气痢);⑥利水通淋(膀胱留热停水、五淋、利小便、利水);⑦通便(大肠秘塞);⑧活血消癥(癥瘕、痃癖、破癥);⑨解毒(消乳痈、解酒毒、解鱼肉诸毒);⑩截疟(痎疟);⑾驱虫(去寸白)。传世的经典名方如二陈汤、苏子降气汤、六君子汤、温胆汤、平胃散等均以陈皮为主药。
五、“陈久者良”之说
“他药贵新,惟此贵陈”。关于陈皮陈久者良的观点,陶弘景首次提出陈皮陈用之说:“凡狼毒、枳实、橘皮、半夏、麻黄、吴茱萸皆须陈久者良,其余须精新也。”此后的本草著作多沿用了这一观点。例如《雷公炮炙论》“其橘皮年深者最妙。”、《汤液本草》“橘皮以色红日久者为佳。”、《本草易读》“色红陈久者佳。”《本草逢原》:“产粤东新会,陈久者良”。《本草品汇精要》:“至十月霜降后已成熟者,味辛而黄大谓之橘皮,医家所用陈皮即经久者是也。”。由此可见,陈皮用陈在南北朝时期便由陶弘景首次提出,以后历代医家和本草借沿袭此说。另外明代的《药鉴》还提出了陈皮的陈放时间要求:“陈皮需用隔年陈”。关于陈皮用陈与用新的区别探讨者甚少,较为代表性的说法是“陈则燥性消,无燥散之患”。《本草备要》:“陈则烈气消,无燥散之患。半夏亦然,故同用名二陈汤。”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收藏又复陈久,则多历梅夏而烈气全消,温中而无燥热之患,行气而无峻削之虞。”。由此,笔者认为“陈久者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久贮陈皮挥发油含量减少,燥性降低;另一方面是久贮陈皮黄酮与挥发油类成分发生变化所致(笔者推断陈皮在久贮陈化过程中,因受环境中黑曲霉相关代谢霉的侵染,其代谢活动不仅导致了陈皮中黄酮类〔橙皮苷、川陈皮素、柚皮苷、橘皮素、槲皮素、芦丁、圣草枸杞苷、四甲氧基黄酮、五甲氧基黄酮〕及挥发油类物质等活性成分的积累,同时还抑制了黄曲霉真菌的生长,降解了黄曲霉毒素,达到增效减毒的效果,从而导致陈皮“陈久者良”)。因此,陈皮既能理气调中,又不因燥性烈而伤阴。其功效侧重于理气调中,用于脾胃气滞诸证达到行气而不伤津耗气的目的。而新产橘皮因其性燥更适用于湿浊中阻之脘腹胀满,恶心呕吐,不思饮食,痰湿壅肺之咳嗽痰多,正是因为二者功用的差异才使得陈皮作为一个药用品种出现。但实际上由于现今用药对新产柑皮的燥烈之性认识不足,现代药典对陈皮的陈用已不做要求。通过对历代本草中陈皮的名称源流、品种、道地性及功效主治的考证,结果表明其都具有本草依据。笔者认为陈皮是我国的传统中药,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至于陈皮陈用与新用,近年来少数药学研究表明,如果用于理气健脾,须陈久者为良;如果用于燥湿化痰,则须去白,然去白者名为橘红,而橘红却无陈久者良之说,则须新用。所以笔者认为陈皮陈放的时间与用药目的有关,主治病证不同,所用陈皮的活性成分比例则需不同。现代研究表明,存放时间长短直接影响陈皮中活性成分的含量比例,且不断转化。但其含量比例变化对药效的影响还需进行大量药效学实验来探讨,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后,方能科学指导用药。综上所述,无论是医学者还是群众们对于陈皮的认识和药食使用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关于青皮入药,根据文献记载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橘树上掉下来的个头很小的幼橘,晒干切片,叫做“个青皮”;一种是个头偏大的,还未成熟的青橘子皮,因常常在果皮上纵剖成四瓣,而称为“四花青皮”。金元时期的张元素著有《珍珠囊》一书,他的徒弟李东垣著有《用药法象》,李东垣的徒弟王好古著有《汤液本草》,三人一脉相承,总结、完善了青皮的用法:“陈皮治高,青皮治低”。陈皮虽然是理气药,但是多用通肺胃之气,治疗咳嗽、胃胀等。但人体的气滞,除了肺胃之外,还有肝,肝气郁滞,初期较轻,爱叹气,或感觉体内有气来回窜动,这种情况用佛手、香橼等疏导就可以了。但肝郁日久,就会加重,表现为胸胁胀痛明显,或者乳房胀痛,或者体内出现包块等等。对于这种较重的肝气郁滞,用陈皮似乎总觉得不赶劲儿,由于五行中,青色入肝,于是,古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比陈皮年轻的青皮……。这段话出自明末医家李中梓,写在《本草征要》中,收录在《医宗必读》里。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而且形象,后来被清代吴仪洛、黄宫绣等多位医家点赞转发。陈皮擅长治疗肺胃,居上焦,所以陈皮治高;青皮擅长治疗肝气郁结,在下焦,所以青皮治低。青皮性味苦辛,微温,有疏肝破气,破气行痰,消积化滞,消痞除满之功效,主要用于胸胁胀痛,胃部痞满,疝气,乳肿,乳核,乳痈,食积腹痛等症。青皮的药用价值主要在于疏肝破气,消积化滞,明白了上述道理,您就能很好理解青皮的功效了。青皮由于年幼少壮,所以性情猛烈,用的好的话,能够行气,过度使用则会破气,甚至出现气虚症状。所以李东垣告诫弟子:“如去滞气用青皮,勿多服,多则泻人真气。”。青皮擅长行肝气,所以常常用于肝气郁滞导致的胸胁胀痛。乳房在肝经上,经常生气,肝郁气滞,容易患乳腺疾病,例如乳房胀痛,或乳房长肿块,在治疗乳腺疾病时,也常常会用到青皮。此外,小肠疝气引起的疼痛也常常是因为气滞导致,但不一定都因生气得病,或是由于着凉导致气滞,也常常用到青皮行气止痛,例如天台乌药散,便是以青皮入药治疗气滞疼痛的名方。青皮治低,对于顽固性腹痛,饮食积滞,大便日久不通的,也可以用青皮消积化滞,甚至体内的包块、肿块,也常常用到青皮。不过青皮性猛,中病即可,不可常用多用。有时为了减缓青皮的药力,处方常常用炒青皮。另外,“四花青皮”由于比“个青皮”老一些,药性也略缓和一些。在具体应用方面,例如很多女性有乳房胀痛之苦,尤其是逢月经则疼痛异常,乳房可以触及肿块。这样的人群,通常都是爱生气,或生闷气或发脾气,或性情急躁,或忧思重重,肝气郁结所致。如前所述,乳房为肝经循行分布区域,肝气郁结最常结在乳房,导致乳房胀痛。遇到这种情况,医院就诊,明确诊断,排除乳腺肿瘤,此外,女性们还应学会乳腺自我检查,并应自我调节,放松心情,排解压力。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用几片炒青皮煮茶饮用,改善症状,如果配合麦芽使用,还能减缓青皮药性,且能疏肝健脾、消食和胃。使用青皮的经典名方有青阳汤、木香顺气散、青皮丸、枳壳青皮饮和大应丸等。此外,根据新会地方史志的记载,青皮主要是四、五月落果或者人为疏果采摘的产物,除少量入药用于治疗上述病症外,大部分还是作香料,用于制作线香。
综上,陈皮的药食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且功效显著,实为不可多得之佳品良药。但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整体观、异病同治、辨症适量使用。
新会陈皮在其药食同源之列中因其药用价值和保健价值,而有“百年陈皮胜黄金,新会陈皮甲天下”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