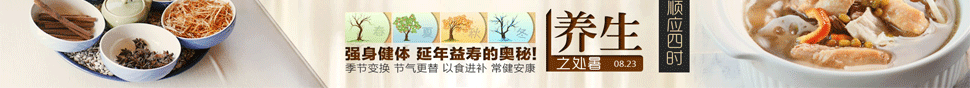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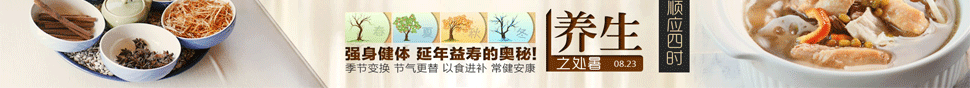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半?夏:供职于云南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出版有长篇小说《铅灰暗红》《忘川之花》《心上虫草》及纪实作品《看花是种世界观》《与虫在野》。近年常行走荒野看花观虫,呼吁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
文/半?夏
时间轴倒序之一:
《中国妇女报》对我的采访
《中国妇女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用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采访稿《从写小说转向博物,通过她的发现,唤起对自然的敬重》,被采访的人是我。采访者是《中国妇女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周玉林先生。这篇文章采写的缘起有两个:一是我在二〇一九年八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与虫在野》,此书出版后获得好评,获得好几个重要奖项;二是我在十月八日于自媒体上发出一个报料——关于外来物种福寿螺对云南玉溪澄江县抚仙湖的疯狂入侵,我的报料引发了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如新华社、今日头条、学习强国、新浪、凤凰等聚焦式报道,澄江县人民政府第二天便向社会表态治理防控福寿螺的决心,承诺拨出专款铲除福寿螺,保护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淡水资源抚仙湖。
两桩事一起采访,文章开头对我的笔名做了一番阐释:“半夏,是一种天南星科药用植物,它生于旷野的田边林下,孤孑骄傲而又婀娜独异。而记者要采访的半夏,却是一位作家——杨鸿雁,笔名半夏。半夏出生于云南的大山里,在云南大学学习了四年的生物学,却做了几十年的新闻人。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是位著作颇丰的长篇小说作者。工作和写作之余,半夏最喜欢的就是走进自然,伏下身,用最近的距离去观看住在高楼里,忙于日常琐碎的我们忽略掉的——虫、草、花、木。”
面对采访者,我直抒胸臆——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至高无上,是这个世界最智慧最了不起的生物,但我要告诉你,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抱着这样的幻想甚至为所欲为,目空一切是不道德的。须知人最终被虫子打败被微生物打败,是完全有可能的……拍摄野花拍摄虫子若只唤起人们发现美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人需要在劳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之外的事物来完善自己的人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里可以找到与自我相处的完美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高尚。现代化的进程,让我们享受了日常的便利、交通的快速和科技带来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改变,同时我们在远离自然,也愈发地妄自尊大了。我写《与虫在野》就是要通过我的发现,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重!
时间轴倒序之二:
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的勇敢发声
记得一九八五年,我读大一时,与几个大学同学骑车从昆明出发,花大半天时间骑行七十公里第一次抵达抚仙湖。从那时候起,抚仙湖这一池晶莹清亮的碧水就一直是淘洗荡涤我身心的好去处,它是硕果仅存的老天给予人间的美好恩赐,而其他的高原湖泊不是水体污染就是水质直接降好多级,要不就是面积缩小,水体盐碱化,处于衰退期。如今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趟抚仙湖畔。有省外或国外的朋友来了,我第一推荐的地方,也必然是离昆明车程仅一小时的抚仙湖。
二〇〇四年,我作为一本刊物的总编助理,曾带着些年轻人去采访世居生活在抚仙湖畔的人们,做一本人文地理类的特刊,抚仙湖湖水的水质是一个重点。记得去到一个当地渔民捕鱼的渔洞时,见一老人家直接用瓢舀起水来就喝,我也走过去手捧起水来就喝。年轻的记者们睁大了眼看着我。我说抚仙湖深,水体量大,自净能力是很强的,没事。他们后来都喝了,当然都没事。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中秋节小假期里,我与家人到位于玉溪澄江县的抚仙湖畔游玩。当我把手机聚焦到湖边湿地的水生植物时,密密麻麻的一团团粉红的东西跳入我的眼帘,我的学科背景与新闻敏感让我一惊,福寿螺?!记得二〇一四年夏天,我在昆明新区呈贡的洛龙公园内首次看见它附着在一丛雨久花露出水面的茎上,当时我还不知道它姓甚名谁,回家查资料得知它是著名外来入侵物种福寿螺的卵块。那次,我也就看见一两处有。没想到,短短几年,它们已“爬”到水质一直保持I类的抚仙湖畔,如此触目惊心!
外来物种的疯狂入侵,抢占本土生存资源,会导致当地生态物种的单一性,而须知在云南九大高原淡水湖泊里,抚仙湖的水体量便占了百分之七十,滇池、洱海、泸沽湖、阳宗海等等其他八大高原湖泊全部加起来的淡水量也不及它的一半,而这九大湖泊中,抚仙湖的水质是最好的。看数据可知,抚仙湖的全部优质淡水可以给十四亿中国人每人分到十五吨可以喝的淡水,它有多重要啊!
可是,如今看着福寿螺这样肆无忌惮地入侵,我担心会引起一系列生态问题。
可为了这池好水我可以做点什么?
我要呼吁当地人迅速铲除它,趁福寿螺集中繁殖的卵块时段集中消灭它。我一直试图向相关部门和几家媒体反映,但没能引起重视。整个假期,我一直惦记着此事,犹如一块石头压在心里,惴惴不安。后来,我从各个角度拍了些图片,在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zhangyebanxiaa.com/bxzz/5278.html


